第十一章 决战上海滩(第7/7页)
撤至第二防线后,中日两军形成了对峙。蔡廷锴在整顿人马,准备重新再战的同时,也非常关心正拟举行的停战谈判。
是不是要割地,要赔款?那是绝对不行的,谁敢这么做,蔡某跟他势不两立。
这么想着,忽然浑身发热,喉咙口疼痛难忍。军医一诊断,才发现是煤炭中毒。
多少天终夜不眠,听报告,作决策,晚上又冷,军部的简陋房子丝毫挡不住寒气,不得不围炉取火。
时间一长,煤火过多,蔡廷锴就中了招。
打仗的时候精神紧张,不知不觉撑住了,现在稍一放松,便给你来个反攻倒算。
蔡廷锴住进了医院,医生要求十日之内不得下床,可是他哪里躺得下来。
前方战事虽停,却成了一个不战不和、不尴不尬的状态,如今日军还占领着上海一大片区域,这是军人之耻。
当总指挥蒋光鼐来看望他时,蔡廷锴紧盯着这位老上司兼老搭档,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三天之内,和战问题仍无法解决,我决定向敌人发起反攻!”
蒋光鼐却躲开了他的眼睛:“凡事你都不要看得太容易,平心静气听候政府处置吧。政府要我们进就进,不要进就不进,万万不可轻举妄动。”
蔡廷锴咬着嘴唇不再说话,但是等蒋光鼐一走,他就掀开被子,从医院里跑了出来。
阅兵,检阅部队。
蔡廷锴看到,经过这些天的补充,第十九路军又呈兵强马壮之势。
他再一次坚定了信心:万一谈判决裂,我仍然可以与敌再战,甚至比以前还要强。
可是蒋光鼐所说的“政府”并不一定这么想。
蔡廷锴是一个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某种程度上,他跟自己的部将翁照垣在性格上倒有些接近,只是更内敛沉稳一些罢了。
现在的行政院院长是汪精卫。蔡廷锴生平最讨厌这个人,偏偏汪精卫还要来前线慰问,作为军事主官,不想陪也得陪。
一共陪了两个小时,对蔡廷锴来说,却犹如过了两年。尤其从汪精卫的言谈举止中,已处处流露出对日妥协的味道,这更让蔡帅甚为不快。
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蒋介石召见他了。此时的蒋介石已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全国军队的当家人。
和“文人政客”汪精卫不同,蒋氏是北伐时的总司令。军人对军人,他一定会像迎接北伐将士归来那样,开心,微笑,然后赞上一句:好样儿的,继续干。
然而没有,都没有。
蒋介石似乎并不高兴,说话时有气无力,临近会谈结束时,最后一句倒很有力,不过却是一句硬邦邦、冷冰冰的话:以后须绝对听从政府命令!
走在回营的路上,蔡廷锴忽然发现他是多么孤独。在领导、同事,很多很多人眼里,自己就是一个狂人,一个完全不顾及后果的狂人。
可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现实让蔡廷锴疼得差点要大声叫喊出来:仗不是我挑起来的,我一片赤诚,为国家争自由,为军人争人格,究竟有什么错?
四周没有回声。
就像那些天的深夜,一个人坐在炉火边。
然而那时候还有暖意,还可以运筹帷幄,现在身旁围绕着的却只有无边的寒冷和寂寞。
这种痛楚,谁能够承受?
停战谈判终于结束了,这就是“淞沪停战协定”。虽然没有割地赔款,但有一个条款对蔡廷锴来说却特别刺目: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中国不得在上海及郊区驻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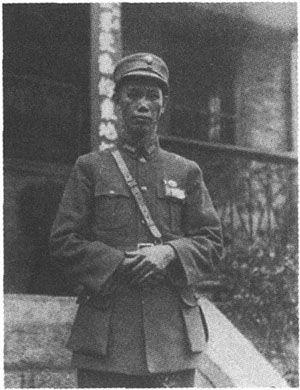
孤独的人是光荣的
我们的血是不是白流了?
蔡廷锴悲愤莫名,却又无可奈何。
一周之后,在苏州召开淞沪抗战烈士追悼大会,面对着黑压压的悼念人群,蔡帅泪流满面,情难自控。
一切都结束了,生活就是这样。
在英国1964年出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蔡廷锴被列为世界名将之一,言其以少敌众、以弱胜强,阻击优势日军达数月之久,为世人所一致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