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迁台前后(第7/9页)
陶孟和最终未被划为“右派分子”,仅为有极右思想的“内控”人员。1960年4月,他在抱病赴上海参加中科院第三次学部会议时,突发急性心肌梗死,于4月17日逝世,享年七十三岁。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在日记中痛惜老同事的骤然去世,笔锋一转又写道:“在反动政府之下则他也已寿终正寝,所以他活到七十三岁高龄仍是受党之赐。”
1951年,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以论文《捺钵与斡鲁朵》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很快就从英国直接回到红旗下的北京。他早已与伯父傅斯年断绝关系。笔者听傅斯年的高足何兹全介绍,1951年,他曾与傅乐焕一起到四川搞土改,何去了南充,傅去了宜宾。估计也去了李庄。但我揣摩傅乐焕的心情定不轻松。他应该目睹或听闻李庄的一系列变化,诸如1940年接纳中研院迁到李庄的国民党区党部书记罗南陔、区长张官周等已被镇压,而他的伯父傅斯年也因脑溢血在台湾猝死……
1952年傅乐焕调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兼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此间,他与史学大师陈垣的侄女结婚,后来有了三个女儿。在相对安静的生活中,傅乐焕埋头治史,先后参加并领导对满族、达斡尔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和调查研究。1966年,“文革”风暴骤至。噤若寒蝉的傅乐焕,成了中央民院首批被揪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他被打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与傅斯年的关系。他被诬为“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陆的特务”。在他的家乡聊城,受清朝皇帝敕封的傅家祖坟被炸药炸开,墓园毁损得面目全非。傅氏族人傅乐新、傅乐铜等均受到冲击。傅乐焕在遭受抄家、批斗、关牛棚等折磨后,身心疲惫。5月23日夜,傅乐焕选择了一片清凉的水域……
天之生才,既予之厚,何夺之速?
三
中研院初到台湾,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史语所考古组研究员石璋如回忆:
民国三十八年阳历二月,刚过完农历新年,史语所搬到杨梅。中博院到台湾之初,先租了铁路局在杨梅的仓库,中博院搬往台中之后,将原先使用的铁路局仓库让给我们。我们租下为铁路局所有、较高大的平房——仓库,作为堆放箱子的地方;民间所有、较低矮的平房——米仓作为办公兼单身同仁的宿舍。在米仓附近还有厨房,也同时在旁边设了饭厅。公家在米仓附近,与大成路、旧镇公所一带租了一批房,再加上原先的公家宿舍,作为从南京来的公务人员的宿舍。29
米仓宿舍,多是楼房,楼下老乡做生意,楼上住公务员。还有人如办事员王志维等就租住堆杂物的号房。曾有一个慈善救济团来到这里,预备帮助史语所改善住宿条件,准备拍照。有人认为已到了这步田地,有什么好照的。夏鼐日记中有高去寻从台湾带过来的一封信。他写道:“终日苦痛(已非苦闷),焦急如待决之囚,两鬓顿成斑白,皆台湾之行所铸造成者也。”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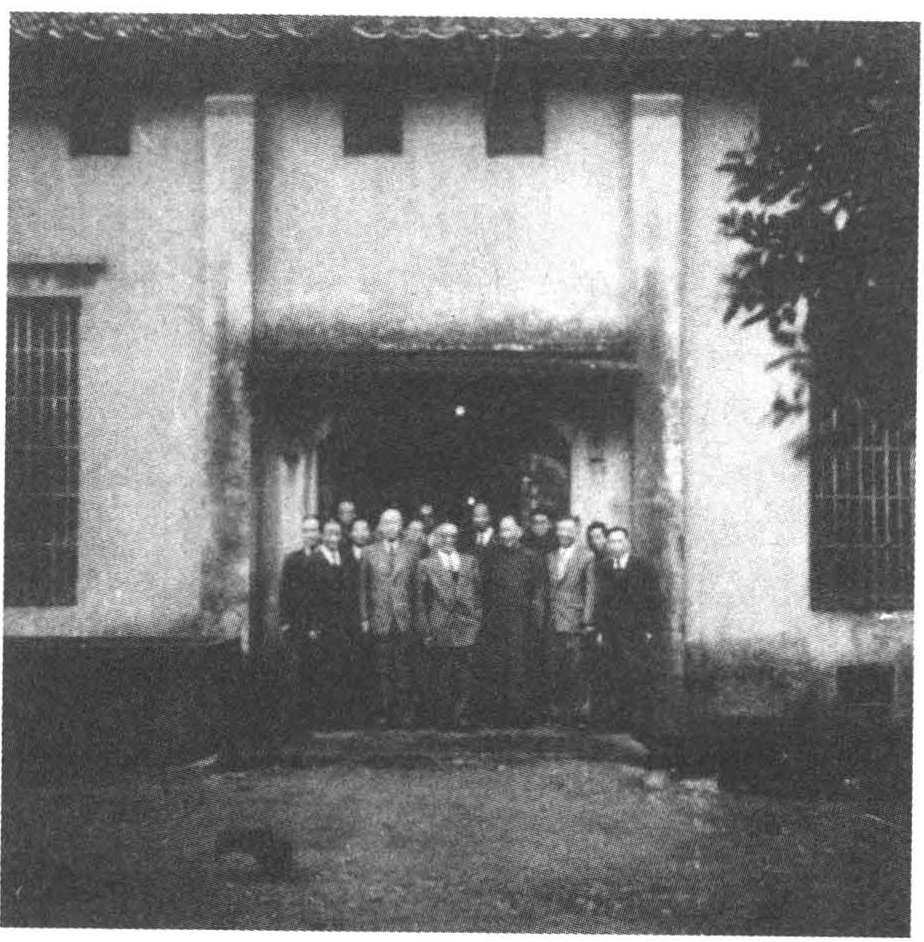
20世纪50年代初,史语所同人在台北杨梅仓库前。(右起)杨时逢、陈槃、芮逸夫、李××、李济、李霖灿、胡适、萧纶徵、朱家骅、×××、李光宇、董作宾、劳榦。
研究员屈万里之妻在《怅望云天》一文中,回忆夫君一段往事:屈家收藏有一张李姓先生赠送的一幅“馈米图”,上有题诗:“天涯老去益相亲,厨冷日长怜我贫。侵晓叩关分禄米,忘他同是断炊人?”其旁加注云:“己丑岁,随孔圣公来台,遭陈蔡之厄,经旬不举火,箧藏鬻质皆空;翼兄先期至,然断贽亦数月矣!所胜者,瓮中尚储米数斗耳,既见予饥,忘己之饥,竟全举以赠,白骨而肉,盛德无以报也。”文字隐曲,说的是李某人1949年渡海来台,遭遇类似孔子陈蔡绝粮的窘境,十多天揭不开锅。屈万里自家存粮不足,但馈赠米面,舍己厚人。
于锦绣随史语所到台湾后,是第一个失去饭碗的人。他系中央政治大学毕业,抗战胜利之时来到李庄,当书记员,顶替离去的书记员杜良弼。当年史语所四组研究员芮逸夫和事务员萧纶徵曾向代所长董作宾写信力荐:“于君学历高,学业优,延补杜君之缺,殊属委屈,承嘱考试成绩亦佳,至于事务室方面似可不必再试,敬乞裁决。”31于锦绣被分到史语所民族学组,跟随芮逸夫深入倮区调查,写成《大小凉山倮罗的社会阶层》一文。1949年2月1日,于锦绣接到史语所的解聘书:“顷奉傅所长面告台端已在遣散之列,自本年二月份起即停止支薪,兹列台端应得之一月份薪及遣散费,款到请查收,再本院总办事处如前有款汇奉,即在此次汇款中扣还,并希查照。”32
傅斯年的绝情无义实属无奈,他自己已是一个泥足巨人。俞大綵曾回忆丈夫傅斯年临终前:“三十九年(1950)十二月十九月,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他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我一阵心酸,欲哭无泪。”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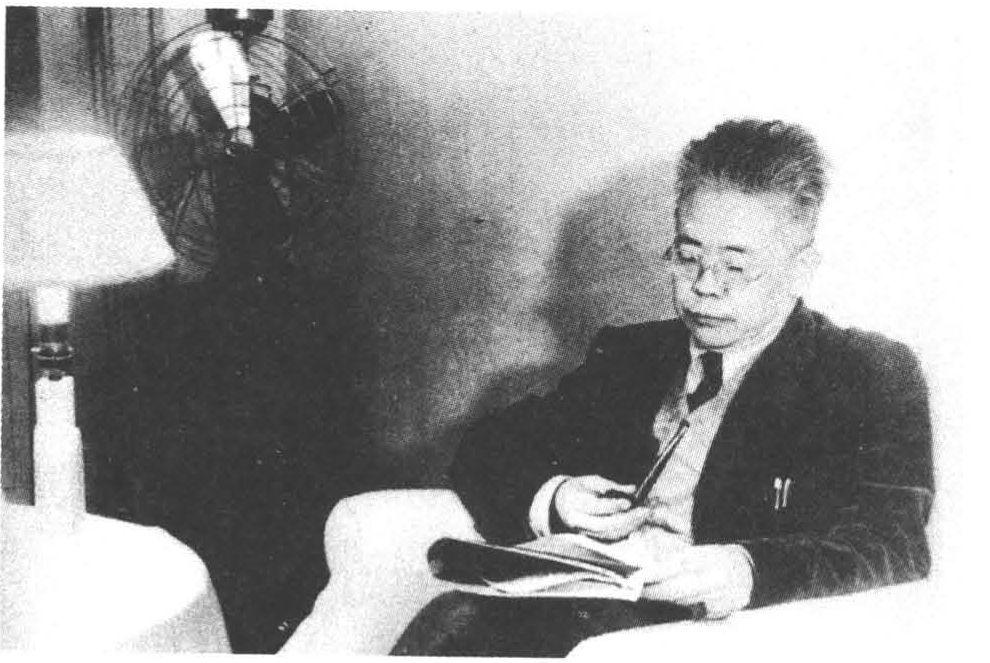
1949年,傅斯年在台大校长室。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赴台湾大学就校长职,仍兼任史语所所长。出掌台大,他广延教授、增建校舍、充实图书、奖励研究,奠定了台湾的学术根基。不久,台湾发生学生运动,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史称“四六”事件。傅斯年十分愤慨,亲自找国民党情治部门交涉,甚至直达最高当局,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确凿证据要逮捕台大师生也必须经本校长批准。当时,国民党政府丢失大陆,退守孤岛,风声鹤唳,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联保制度,也要求台湾大学师生办这种手续。傅斯年挺杖而出:凡是在台湾大学任教和服务的教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他可以个人作保。若有问题,愿负全部责任。结果台湾大学破例没有实行联保制度。1949年7月11日,有人在台北《民族报》发表《寄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论反共教育与自由主义》,指控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后,将自由主义作风带到台湾来,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所聘教授中,竟有共党分子和亲共分子,以致学校成为政治上的特区,院系成为共产党细菌的温床,赤焰相当高涨。傅斯年发表了《傅斯年校长的声明》和《傅斯年校长再一声明》,他写道:“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他的最后一次讲话,在重申自己的办学原则和育人理想之后,情绪激昂地说,“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们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摈弃于校门之外。”